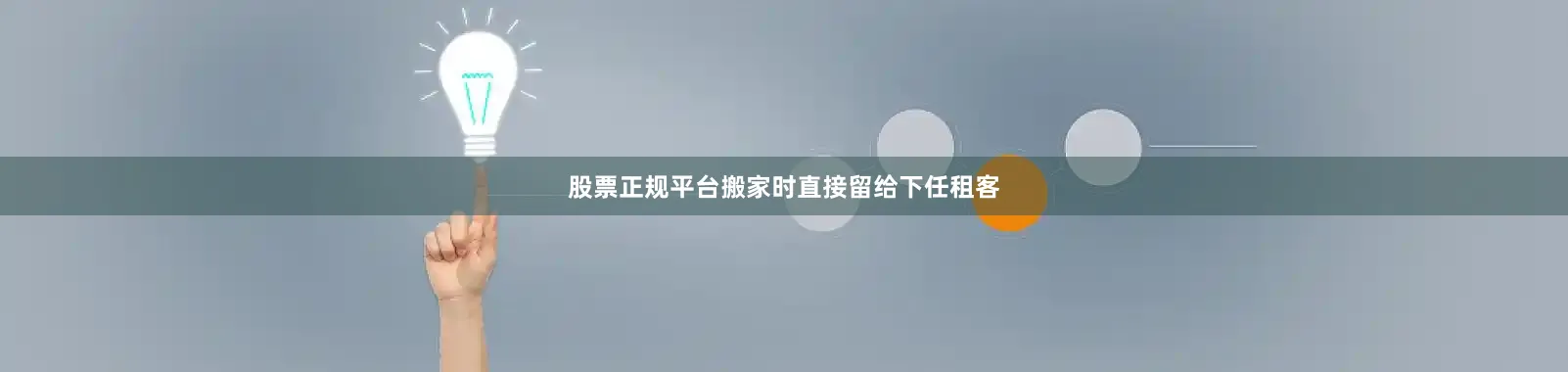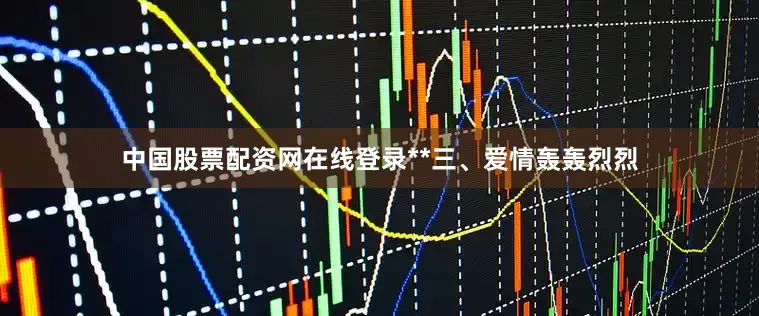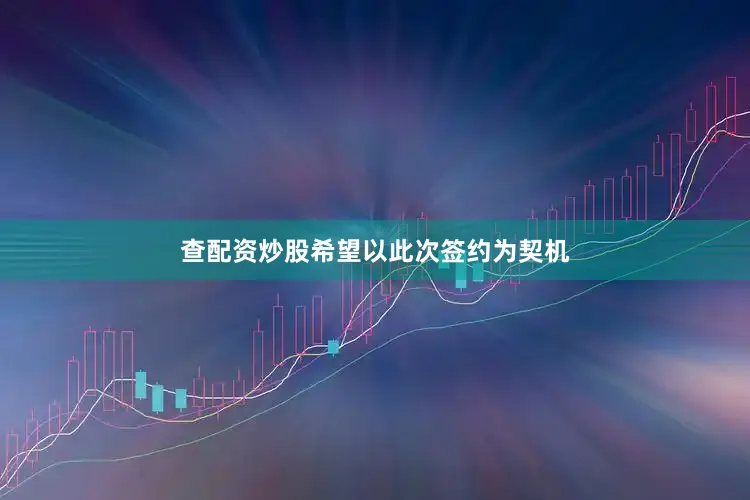01
1927年9月23日,江西萍乡芦溪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与硝烟味,混杂着南方初秋湿冷的泥土气息。一支残破的队伍正在艰难地行军,士兵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,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和疲惫。
他们的军装早已被撕扯得不成样子,泥浆、血污和汗渍凝结成了硬块,紧紧地贴在身上。许多人光着脚,在崎岖的山路上留下一个个血印。
这就是秋收起义的部队,一支刚刚从浏阳城下惨败下来的军队。
队伍的后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,像是有人在身后猛地敲响了催命的丧鼓。
「敌袭!敌袭!」
尖锐的喊声划破了队伍死一般的沉寂,原本麻木的士兵们瞬间被恐惧攫住,队伍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。
负责殿后的第三团乱作一团,士兵们如同受惊的鸟兽,四散奔逃。
「不准退!顶住!给我顶住!」
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从队伍中冲了出来,他的声音嘶哑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他就是这次起(义)的总指挥,卢德铭。
卢德铭腰间的驳壳枪已经上膛,他一边组织身边为数不多的警卫人员构筑防线,一边对着溃散的部队大吼。
「我们是工农革命军!身后就是毛委员!谁敢后退一步,就是把刀递到敌人手上!」
他的话语像一剂强心针,让一些惊慌失措的士兵暂时稳定了下来。然而,敌人的火力异常凶猛,子弹像雨点一样泼洒过来,不断有人中弹倒下。
情况万分危急。
卢德铭很清楚,如果殿后部队彻底崩溃,那么整个起(义)的火种,包括那位正在队伍前方思索着这支军队未来方向的毛委员,都将被这股追兵彻底扑灭。
他没有丝毫犹豫,亲自端起一支步枪,依托着一处小小的土坡,开始向敌人精准还击。
「砰!」
一名冲在最前面的敌军军官应声倒地。
卢-德-铭三个字,在当时的黄埔系和北伐军中,本身就是一个响亮的名号。他枪法精准,作战勇猛,是叶挺独立团打出来的名将。
在他的带动下,残余的士兵终于鼓起勇气,开始零星地还击。
然而,敌人的数量太多了。
枪声越来越近,卢德铭感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他不断地变换着位置,试图吸引敌人的主要火力,为部队主力的转移争取哪怕多一秒钟的时间。
突然,他感到右胸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,仿佛被一柄烧红的铁锥狠狠刺穿。
他低头看去,鲜血正从军装的破口处汹涌而出,迅速染红了整个前胸。
他的身体晃了晃,手中的步枪再也握不住,无力地掉落在地。
意识开始模糊,耳边的枪声、喊杀声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。他最后的视野里,是那面残破却依旧在风中飘扬的红色旗帜,以及队伍向着远方山林转移的模糊背影。
他知道,他们安全了。
当消息传到队伍前方时,那位后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毛委员,猛地停下了脚步。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一遍又一遍地向传令兵确认。
当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后,这个意志如钢铁般的男人,双眼瞬间通红,他对着苍茫的群山,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悲痛至极的呼喊:

「还我卢德铭!给我三个师也不换!」
这声呼喊,饱含着巨大的悲伤与惋惜,穿越了历史的风雨,也留下了一个久久未能解开的疑问:这位年仅22岁就壮烈牺牲的总指挥,这位让毛泽东发出如此痛惜之言的军事搭档,如果他没有倒在芦溪的那个土坡上,如果他能活到1955年,他的胸前将会佩戴上怎样的勋章与军衔?
02
要解答这个疑问,我们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——1927年的那个血色夏天。
那是一个天与地都仿佛被血染红的季节。
蒋介石在上海发动「四一二」,汪精卫在武汉发动「七一五」,屠刀挥向了昔日的盟友。一时间,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了整个中国,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河。
然而,压迫越是深重,反抗的火焰就越是炽烈。
在南昌城头,一声枪响划破了沉沉的黑夜,那是贺龙与周恩来、朱德、叶挺等人,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。这支军队,成为了后来人民军队的源头之一。
贺龙,这位南昌起(义)的总指挥,也是四大起(义)总指挥中,唯一一位走到了革命胜利终点的人。他的人生轨迹清晰而辉煌,红二方面军总指挥、八路军120师师长、西南军区司令员……每一个职务都刻印着他为这个国家立下的赫赫战功。1955年,他被授予元帅军衔,实至名归。
他的幸存,反而衬托出另外三位总指挥的牺牲是多么令人扼腕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当南昌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时,另一场更为重要的起(义)正在湘赣边的田埂上酝酿。
这就是秋收起(义)。
而领导这场起(义)军事行动的,正是卢德铭。
卢德铭,1904年出生于四川自贡的一个富裕家庭,但他却早早地走上了一条为穷苦大众谋解放的道路。1924年,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,与后来的陈赓、许继慎等人成为同学。
在黄埔,他不仅学习了最先进的军事理论,更重要的是,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,并迅速成为了坚定的信仰者。
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。
那是一个怎样的英雄团体?
在北伐战争中,独立团一路披荆斩棘,从汀泗桥到贺胜桥,再到武昌城,打出了「铁军」的威名。而卢德铭,就在这支铁军中担任营长,屡立战功,年纪轻轻就已是声名鹊起的青年将领。
1927年6月,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了加强自己的卫戍力量,在武昌成立了警卫团,卢德铭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黄埔背景,被委任为团长。
这个警卫团,表面上是张发奎的部队,实际上却由我党牢牢掌控,宛如一把插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利剑。
按照原计划,卢德铭是要率领这支精锐部队参加南昌起(义)的。
然而,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做出了不同的安排。
由于消息传递的延误,当卢德铭在8月2日得知起(义)消息时,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。
他心急如焚,立刻率部向南昌疾驰,但当他们赶到江西九江时,却得知起(义)部队早已南下,而沿途布满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。
前路已断。
卢德铭当机立断,与团里的几位干部化装成商人,秘密返回武汉,向组织请示下一步的行动。
正是在那里,他接到了一个新的,也是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命令——率领警卫团,前往湘赣边,配合即将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(义)。
他被任命为起(义)总指挥。
于是,历史的舞台上,两位伟大的身影第一次交汇了。一位是崭露头角的军事将领,一位是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家。
他们成为了彼此的第一位军事搭档。
03
秋收起(义)的家底并不算雄厚,总兵力近5000人。
这其中,卢德铭率领的原警卫团就有2000多人,装备精良,训练有素,是绝对的主力部队和战斗核心。
可以说,没有卢德铭和他带来的这支部队,秋收起(义)的军事基础将无从谈起。
起(义)初期,进展得还算顺利。

然而,很快,部队就遭遇了巨大的困难。按照上级「取浏阳攻长沙」的指示,起(义)军向坚固的城池发动了猛攻。
结果可想而知。
在装备、兵力、训练都远超自己的敌人面前,这支年轻的革命军队撞得头破血流。
浏阳一战,起(义)军伤亡、溃逃的人数超过了一半。部队的士气,瞬间跌落到了冰点。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,未来的道路,一片迷茫。
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还要继续攻打长沙,无异于以卵击石,自取灭亡。
就在这支军队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,一次激烈的争论爆发了。
地点是在一个小村庄的祠堂里。
昏黄的油灯下,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,气氛凝重得几乎让人窒息。
毛泽东首先发言,他的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坚定。
「同志们,事实已经证明,我们目前的力量,还不足以攻占像长沙这样的大城市。继续打下去,只能是全军覆没。我建议,我们放弃攻打长沙,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,去开辟新的根据地,保存革命的火种。」
这个观点,在当时无异于一声惊雷。
因为共产国际和上级的指示,就是要在大城市发动起(义),夺取中心城市。向农村转移,在很多人看来,就是一种逃跑,一种失败。
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立刻站了起来,他也是黄埔生,性格高傲,他几乎是拍着桌子反驳:
「毛委员,这是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!我们的任务就是夺取长沙,现在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,就是逃兵主义!我坚决反对!」
余洒度的发言,代表了当时军中不少指挥员的想法。他们大多是正规军校出身,接受的都是攻城略地的传统军事思想,对于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,既不理解,也看不起。
双方的争论瞬间变得白热化,祠堂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。
支持余洒度的人不在少数,他们认为毛泽东一个不懂军事的「师爷」,是在瞎指挥。
毛泽东据理力争,但场面一度陷入僵局。
这支刚刚诞生的革命军队,面临着第一次因为路线分歧而分裂的危险。
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,一直沉默不语的总指挥卢德铭,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所有人的目光,瞬间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。
作为军事总指挥,他的意见,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他先是看了一眼情绪激动的余洒度,然后将目光转向了神情凝重的毛泽东。
他开口了,声音沉稳而有力。
「我同意毛委员的意见。」
仅仅一句话,就让整个祠堂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他接着说道:
「打仗,不是为了赌气,更不是为了盲目地执行命令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?是保存革命的力量,最终取得胜利。现在长沙城下,敌人重兵集结,我们去打,就是送死。军事上,这是绝对不可行的。」
「毛委员提出的向农村进军,是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。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这支队伍还在,革命的火种就在。我作为总指挥,必须为所有战士的生命负责!」
卢德铭的发言,掷地有声。
他不仅是军事主官,更重要的是,他深刻理解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精髓。他看到了城市中心论的弊端,也看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。
他的支持,是决定性的。
它不仅仅是军事指挥员对政治委员的支持,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,以其专业的判断,为一条全新的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道路,投下了最重要的一票。
正是因为他的鼎力支持,这场几乎要将起(义)部队拖入深渊的争论才得以平息,部队最终得以统一思想,向着井冈山的方向,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。

可以说,在那个决定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夜晚,卢德铭用他的远见和担当,挽救了这支军队。
然而,命运是如此残酷。
仅仅几天之后,这位刚刚为革命拨正了航向的年轻将领,就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。
他的牺牲,是秋收起(义)乃至整个人民军队早期历史上,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损失。
04
当我们回望历史,试图去构想卢德铭如果活下来的另一种可能时,我们不妨看一看,当时在他麾下的那些年轻人的名字。
在秋收起(义)的队伍里:
罗荣桓,只是一名小小的连党代表。
谭政,是师部的文书。
张宗逊,是一名连长。
陈伯钧,是一名排长。
而黄永胜和陈士榘,仅仅是班长。
宋任穷,则是农民自卫军一个中队的党代表。
这些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,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将帅星辰中耀眼的存在。
而卢德铭,是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。
他的起点,是如此之高。
更重要的是,他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近乎完美的配合与信任。一个制定战略,一个指挥战斗;一个把握方向,一个冲锋陷阵。这种「毛卢搭档」,如果能够持续下去,其产生的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。
在井冈山时期,在后来的反「围剿」中,在长征路上,卢德铭无疑将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。他黄埔科班出身的军事素养,加上在实战中与毛泽东思想的不断磨合,极有可能让他成为我军早期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。
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如果历史的轨迹稍有不同,卢德铭将会有更大的舞台,去施展他卓越的军事才华。
因此,如果他能顺利地走到1955年,以他的资历、战功,以及与统帅的深厚渊源,授予大将军衔,是大概率事件。
甚至,考虑到他在初创时期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,以及毛泽东那句「给我三个师也不换」的极高评价,元帅的行列中,出现他的身影,也并非没有可能。
可惜,历史没有如果。
就在卢德铭牺牲后不到三个月,在千里之外的鄂豫边界,另一场惊天动地的起(义)爆发了。
这就是黄麻起(义)。
这场起(义)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其历史地位都被低估了。但它的意义却无比重大,因为它直接催生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。
从黄麻起(义)的队伍里,走出了徐海东、王树声两位大将,以及许世友、王宏坤等九位上将。将星璀璨,可见一斑。
然而,这次起(义)的总指挥,潘忠汝,他的名字却远不如卢德铭那样广为人知。
潘忠汝,1906年出生于湖北黄陂。他的人生轨迹与卢德铭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1926年,他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,同样是一位满怀报国热情的青年军官。
大革命失败后,他接受组织派遣,进入黄安县公安局担任军事教练,利用这个身份秘密发展党员,积蓄革命力量。
当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而来时,他没有丝毫畏惧,毅然带领一批公安局的骨干,加入了黄安农民自卫军,并担任大队长。
1927年11月初,湖北省委的密令传来,要求黄安、麻城两县举行武装起(义)。
两县的革命力量迅速整合,成立了黄麻起(义)指挥部。年轻的潘忠汝,因其军事才能和果敢的作风,被一致推选为总指挥。

11月13日晚,起(义)爆发。
潘忠汝身先士卒,带领起(义)军迅猛地攻占了黄安县城,建立了鄂豫边界的第一块红色政权。
然而,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。
敌人的反扑,来得异常迅速和凶猛。
国民党第12军的教导师,一个装备精良的王牌部队,如同饿狼一般扑向了刚刚获得新生的黄安城。
12月5日晚,激战爆发。
起(义)军虽然英勇,但毕竟刚刚组建,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经验,都与敌人相差悬殊。
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,黄安城危在旦夕。
在最危急的关头,潘忠汝本来完全有机会率领一部分主力突围出去,为革命保留火种。
但是,他看着城中那些尚未撤离的同志和群众,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悲壮决定。
他要回去,救出更多的人。
他就像古代演义中的赵子龙,单人独骑,杀入重围。
他带领着一支敢死队,一次又一次地冲进已经被敌人占领的街巷,硬生生地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一批批同志。
据幸存者回忆,那个夜晚,潘忠汝在黄安城里,足足杀了六个来回。
他浑身浴血,状若战神,让敌人闻风丧胆。
然而,人力终有穷尽。
就在他第七次冲进城里,试图救出最后一批被困同志时,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。
这位年仅21岁的总指挥,轰然倒下。
他的牺牲,是如此的壮烈。
潘忠汝不像卢德铭,在北伐战争中就已声名显赫,他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伟大搭档来衬托他的光芒。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,他尚未完全施展出自己的才华。
因此,如果以1927年时的资历和地位来衡量,他如果能活到1955年,被授予上将军衔,是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推断。
但历史同样也充满了变数。黄麻起(义)走出的红四方面军,以骁勇善战著称,如果潘忠汝能一直领导这支部队,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建立更大的功勋,他的成就上限,未尝不能触及大将的门槛。
05
最后,我们来看广州起(义)。
这次起(义)的总指挥,是叶挺。
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,如雷贯耳的名字。
如果说卢德铭和潘忠汝的军衔还需要我们去推测和论证,那么叶挺,如果他能参加授衔,元帅军衔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他的资历太老了。
早在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时期,他就是广州总统府警卫团的营长,是孙中山最信任的青年军官之一。
北伐战争中,他率领的独立团,更是整个北伐军的先锋和利刃,「铁军」的称号,就是从他这里叫响的。
南昌起(义)时,他是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。虽然从人数上看,他的11军不及贺龙的20军,但论战斗力和精锐程度,装备着德式武器的11军,无疑更胜一筹。
而广州起(义),更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——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,第一次正式使用「红军」的称号。
在此之前,南昌起(义)沿用的是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」的番号,秋收起(义)则称为「工农革命军」。
「红军」二字,始于广州。
因此,毛泽东曾经当面称赞叶挺:

「你是红军的第一任总司令,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。」
这样的评价,份量何其之重!
无论是南昌起(义)还是广州起(义),叶挺都处于最高领导层。在军队初创时期的地位,即便是后来的十大元帅,在当时也无人能及。
他不仅在我党我军中威望极高,在国民党方面,也被公认为一代名将。
抗日战争初期,新四军军长的人选,国共双方争执了很久,谁也不同意对方的人选。直到最后,有人提议由叶挺出任,双方才都没有了异议。
这个细节,足以证明叶挺在当时中国军界的地位。
后来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,是元帅。
在新中国评选的36位军事家中,叶挺也赫然在列。
综合以上所有因素,如果1946年那架飞往延安的飞机没有失事,叶挺活到了1955年,他极大概率会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但是,历史的复杂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。
叶挺的革命生涯中,也存在着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,那就是他曾脱党近十年。
从广州起(义)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,这中间最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,他没有参与。开辟革命根据地、独立领导一方军事斗争的功劳,他也是缺失的。
这一点,与另外九位元帅相比,是一个明显的短板。
即便是在他担任军长的新四军中,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扰。
由于当时他尚未重新入党,他无法参加党委会。这意味着,新四军的核心决策,他都无法参与。大小事务,基本都由政委项英负责。
这让满怀报国热情的叶挺感到极度痛苦和压抑,他甚至多次提出辞职,以示抗议。
权力实际上被架空了。
因此,也有一种观点认为,即便叶挺没有牺牲,到了解放战争时期,他也需要像其他高级将领一样,去负责一个大的战略区,指挥几场决定性的大战役,打出实实在在的战绩,才能真正让人信服。
否则,以他特殊的经历,也有可能转到行政岗位,不参与军队的授衔。
当然,这只是一种基于历史复杂性的分析。
更大的可能,是党和人民会充分考虑到他在建军时期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威望,授予他应得的荣誉。
06
三位总指挥,三种不同的人生轨迹,三个令人扼腕的结局。
卢德铭,倒在了为革命寻找正确道路的黎明前夜。他的牺牲,换来了井冈山红旗的飘扬。
潘忠汝,倒在了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血战之中。他的鲜血,浇灌出了后来强悍的红四方面军。
叶挺,倒在了抗战胜利后飞往延安的途中。他的归来,本应是革命力量的一次巨大融合。
他们的人生,都定格在了革命的半途。
他们的故事,是那个大时代无数悲壮史诗的缩影。
历史的长河,由无数的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。我们今天回望这些早逝的英雄,去探讨他们未竟的功业,并非是为了给历史做一个冰冷的「如果」,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,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,是建立在怎样巨大的牺牲之上。
那些在1955年站在授衔台上的将帅们,他们的肩上,不仅仅承载着自己的功勋,更承载着像卢德铭、潘忠汝、叶挺这样无数牺牲战友们的未竟理想。
每一颗将星的闪耀,都映照着另一颗过早陨落的星辰。
这,或许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,最深沉的回响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 1.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》 2.《秋收起义》历史资料 3.《叶挺传》 4.《红四方面军战史》 5.《中国工农红军人物志》
互联网股票配资,杠杆炒股官网,配资平台查询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